沉默了好一段時間,事緣是因為筆者最近忙於翻譯聖禮部部長薩拉樞機 (Cardinal Robert Sarah) 早前的一段講話。這段講話是樞機在一個在德國舉行的「未來的泉源」 (“Source of the Future”, “Quelle der Zukunft”)研討會所講的。
該研討會是回應着今年2017年7月7日將是教宗本篤十六世頒布《歷任教宗》自動手諭十周年,將羅馬禮特殊形式 (Extraordinary Form of the Roman Rite,或稱傳統羅馬禮) 恢復到一個能恆常地舉行的情況。然而,即使我們未必很常參與羅馬禮特殊形式,甚至一次也沒有參加過,但教宗本篤十六世卻指出,新禮和舊禮兩種形式應該要有「互相增益」 (mutual enrichment),所以即使我們單單只參與新禮的彌撒,《歷任教宗》也確確實實地影響我們的禮儀生活。
薩拉樞機的這篇講辭雖然提到傳統羅馬禮,但事實上,他更集中於禮儀的本質,對每個教友認識禮儀、參與禮儀都有莫大的益處。
我們討論禮儀,很容易流於表面,討論禮節中不同的細節。因為這些是標記,在本質上是容易看見的事物。但實際上,禮儀的本質是以標記進入天主的奧跡之中。而薩拉樞機這次的講話中,正正就是提醒我們,本篤教宗將羅馬禮特殊形式帶回教會主流當中,正正是要讓所有信友從新在禮儀中獲得靈修的養份,真正透過禮儀跟天主相遇。
我的 重點 及[註腳]。
本篤十六世頒布《歷任教宗》十周年 「未來的泉源」研討會 聖座禮儀及聖事部部長 羅伯特.薩拉樞機 開幕辭 2017 年 3 月 29 日 黑撒根拉特,鄰近阿亨巿 #
譯自 Catholic World Report 的英文翻譯: http://www.catholicworldreport.com/2017/03/31/cardinal-sarahs-address-on-the-10th-anniversary-of-summorum-pontificum/ 中文譯文全文

首先我願意由心底感謝在教宗本篤十六世頒布《 歷任教宗》自動手諭 ( Motu proprio “ Summorum Pontificum”) 十周年,在黑撒根拉特舉辦「未來的泉源」研討會的主辦人,他們讓我在你們反省這個題目時給予一個介紹, 這題目對教會的生命很重要,尤其是對禮儀的將來;我很高興能給你們一個開幕辭。我願親切地歡迎這研討會的所有參加者,特別是以下這些團體的成員,我特別提到你們因為你們很有心地邀請了我: 德國 Una Voce ;漢堡及科隆總教區司鐸及平信徒公教圈 (The Catholic Circle of the Priests and Laity of the Archdioceses of Hamburg and Cologne)、紐曼樞機協會(The Cardinal Newman Association)、黑撒根拉特聖日多達堂的神父網絡 (The Network of the priests of Saint Gertrude Parish in Herzogenrath)。當如我寫信給黑撒根拉特聖日多達堂的主任司鐸 Guido Rodheudt 神父時表示,我很抱歉我得放棄參加你們的研討會,因為在我已經很忙碌的日程中,有一些突發的事務再出現了。但無論如何,我仍透過祈禱在你們中間:這會每天伴着你們,當然你們也會在研討會的日程,即3月29日至4月1日,我每天奉獻的彌撒聖祭的奉獻當中。所以我會盡我所能,替你們的研討會日程作一個開始, 反思一下《歷任教宗》自動手諭在團結及和平中實行的方式。
正如你們所知,在二十世紀初的所謂「禮儀運動」,就是聖教宗庇約十世 (St. Pius X)的一個意向,這在《在關懷中》自動手諭 (1903) ( Motu proprio “ Tra le sollecitudini”) 中表達了出來,就是要恢復禮儀而讓它的寶藏更讓人容易獲取,終能使禮儀再一次成為真正基督徒生命 (authentically Christian life) 的源頭。因此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 禮儀憲章》 ( Sacrosanctum Concilium) 中,禮儀的定義就是「教會生命及傳教使命的高峰及泉源」﹝見第10條﹞。 我們得不斷重覆說:為教會的高峰和泉源,禮儀的基礎就是基督自己。 事實上,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新而永久盟約的唯一及永恆的大司祭,因為祂在奉獻中獻出自己,「衪只藉一次奉獻,就永遠使被聖化的人得以成全」(希伯來書 10:14)。因此《天主教教理》宣告:「教會在禮儀中宣布和慶祝的就是基督的奧跡,為使信友能在世界上見証這奧跡,並依此生活」(第1068條)。 這「禮儀運動」,它其中一份最佳的果實就是《禮儀憲章》,就是我們要考慮在2007年7月所頒布的《歷任教宗》自動手諭時的背景;[樞機要表達一點:由《在關懷中》,到《禮儀憲章》,到《歷任教宗》,教會對禮儀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當然這不排除教會在歷史的過程中因發現信友或神職的執行有偏差而有不同的著眼點。但我們不應因自己短短十年八年的經驗來斷言教會對禮儀的看法。反而我們需要尋求一種詮釋法是能夠貫通整個「禮儀運動」至今的發展,才能理解教會對禮儀更新的看法。] 我們今年很高興懷着大喜樂及感恩的心情去慶祝它的頒布十周年。因此我們可以說聖教宗庇約十世所開始的「禮儀運動」從沒有中斷過,而在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推動下更在我們的日子中繼續。在這主題上我們可以提到 他作為教宗舉行神聖禮儀時的特別小心和個人的專注、經常提到禮儀作為教會生命的中心的講話、以及最後他的兩份訓導文件 (Magisterial documents) 《愛德的聖事》 ( Sacramentum Caritatis) 及《歷任教宗》。 [本篤教宗本身是神學家,他並不以規律去指揮教會,卻以自己的言行作示範。所以我們要理解本篤的禮儀觀,不能按他立了甚麼禮儀法則,卻應留意他舉行禮儀的方法、態度,以及他的訓導。] 換句話說,禮儀中的 「更新」( aggiornamento)1 所指的, 在特定層面上被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自動手諭《歷任教宗》所完滿了。這是甚麼一回事呢?榮休教宗分別了同一羅馬禮的兩種形式:稱為「普通形式」 (“ordinary” form) 的就是按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指引所修訂的《羅馬彌撒經書》的禮文、和稱為「特殊形式」 (“extraordinary”) 的就在禮儀「更新」前所用的禮儀。因此,在羅馬/拉丁禮中,現行有兩本彌撒經書:真福保祿六世頒布而在2002年有第三版的彌撒經書、及聖庇約五世頒布而最後被聖若望二十三世在1962年頒布最後版本的彌撒經書。

在附於其自動手諭的《 致各主教函》( Letter to the Bishops Accompanying Summorum Pontificum) 中, 教宗本篤十六世清楚地解釋了他決定讓兩本《彌撒經書》的目的不單單是為了滿足那些附屬於(attached to)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禮儀的信友團體的願望,更是為了讓羅馬禮的兩種形式能夠相互增益 (mutual enriching)[即是說,羅馬禮特殊形式不是為了「懷舊」,事實上這是很愚蠢的說法;卻是為了禮儀發展的將來。所以,將羅馬禮特殊形式常規化不是追憶過去,卻是為了踏步將來。];換句話說,不單為了他們的和平共存,也為了藉着強調兩者的優點而完滿它們的可能性。他特別寫出:「 羅馬禮的兩種形式,實可互相增益:新聖人和新頌謝詞,其實可以亦應該納入舊彌撒經書中……而按照保祿六世彌撒經書所舉行的彌撒,將較以往更有力地展現那吸引這麼多人返回舊禮的神聖性。」這些文字就是榮休教宗用以表達他對重新啟動「禮儀運動」的渴望。 在那些可以實施這自動手諭的堂區,牧者們見證了信友間及神父間出現了更大的熱忱,一如 Rodheudt 神父自己能夠作證。 他們也留意到按普通形式所舉行的感恩祭有着變化及正面的靈修發展,尤其是重新發現了對至聖聖體表達崇敬的姿勢:下跪、單膝跪等等,也因着在彌撒聖祭重要時候的神聖靜默所帶出更收歛的心神,這樣 使神父們和信友都能更內化被慶祝的信德奧跡。的確,禮儀及靈修培育必須鼓勵及宣傳。同樣地有需要的,是去推廣一個全面修訂的教育法,為了要超越一個過於規範的「禮節主義」去給不熟悉或那些只是部分熟悉的人解釋特倫多彌撒經書……而他們的認識可能有偏見。要這樣做的話,就有急切需要去完成一本拉丁/本地語雙地語的彌撒經書,使信友在感恩聖祭的參與能夠更加完滿、有意識、親密以及有果效。而以恰當的禮儀教理去強調兩本彌撒經書的連續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神父作證說這工作非常有挑戰性,因為他們有意識地為禮儀更新工作、為我們剛剛提到的「禮儀運動」貢獻自己的能力;換言之, 事實上教宗方濟各積極地召叫我們作這神修及靈修的更新,這也是帶有傳教意義,也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意願 (in other words, in reality, to this mystical and spiritual renewal that is therefore missionary in character, which was intended by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to which Pope Francis is vigorously calling us)。 因此禮儀必須經常革新以更忠於它的神修本質 (mystical essence)。 但大多數時間,取代了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希望的「修復」的「革新」只是以表面的精神所執行,而它單獨只按一個原則進行:就是不顧一切地壓抑傳承,這傳承被視為全然負面及過期的,所以一道鴻溝被加於大公會議之前及之後的時間中間。[這就是所謂的 傳承詮釋法 及斷裂傳釋法的分別。]現在只需再次拿起《禮儀憲章》並 誠實地閱讀,不要扭曲它的意思,就能看到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 真正目的 並不是開啟一個斷裂傳統的一個革新,正正相反,卻是要重新發現並確認按最深厚意義理解的傳統。 事實上,按本篤十六世的訓導 (Magisterium of Benedict XVI) 的說法:「革新中的革新」 (“the reform of the reform”),這可能應更準確地稱為「禮儀的相互增益」(“the mutual enrichment of the rites”),首先是一個靈修需要。 而明顯地這與羅馬禮的兩種形式有關。對待禮儀的特別關注,即對重視禮儀的急切性、為它的美及神性特質工作、及在忠於傳統及合法發展兩者之間取得一個正確的平衡,而因而絕對及從根本地拒絕任何斷裂傳釋法:這些重要的元素全是所有基督徒禮儀的中心。若瑟.拉辛格樞機不倦地重覆着震撼着教會五十年的危機,這大約由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開始,跟禮儀的危機有關係,因此也延申到對神聖朝拜的重要元素缺乏尊敬、去神聖化、以及最終的將它們推倒。 「我相信,」他寫道「我們今天所經驗到教會的危機很大程度是由於禮儀的瓦解。」 2

當然,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希望推廣天主子民在禮儀的更大的主動參與及在信友的基督徒生命中日新又新地帶來進步(參閱《禮儀憲章》第1條) 。當然,有些意念是出自這些條文。但是面對着按生活禮儀的現代推廣者的意見而更改的教會禮儀所引起的災難、破壞、及分裂,我們不能視若無睹。 他們忘記禮儀行動不單是一個祈禱,最重要的這是一個奧跡,在當中有一些事為了我們的益處完成了,但我們卻不能完全理解,我們卻必須接受並在信、愛、服從及朝拜的靜中所領受。這才是信友「主動參與」的真正意思。[我們以為我們要明白,才能參與禮儀;所以我們要將禮儀弄得淺白,「畫公仔畫出腸」,但這種想法卻忽略了禮儀是 opus Dei ,天主的工作,我們不可能完全明白,但因着天主的邀請,我們將能在這奧秘中跟天主相遇。]這不是單純關乎外在行為、在禮儀中分派角色或工作,卻是關乎於一個深切主動的領受:這領受,在基督內及偕同基督的,是在靜默的祈禱及透切的默觀態度中的謙遜地奉獻自己。嚴重的信仰危機不單在基督信友的層面,卻尤其發生在很多神父及主教身上, 這信仰危機使我們無法理解感恩祭禮儀是一個祭獻——即耶穌基督一次而永遠地為所有人而行的——藉着教會在不同的年代、地點、民族及國家中使十字架的祭獻以不流血的方式臨現。現在很多時都有一個褻聖的傾向,就是矮化彌撒聖祭成為一個友愛的聚餐、一個世俗的慶典、一個團體的自我慶祝、甚或更差而成為為逃避生活磨難而分散注意力的機會,當中已毫無意義或失去了面對面見到天主的敬畏,事實上祂的目光揭示及命令我們真實而毫不掩飾地望着我們內在生命的醜陋。 但彌撒聖祭不是一個分散我們注意力的時間。這是為使我們由罪惡及死亡中得救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生活祭獻,全是為了揭示着天主父的愛及光榮。 很多天主教徒不知道每一個禮儀慶典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光榮及朝拜天主、拯救及聖化人類,因為在禮儀中「在完善的光榮天主,使人聖化」(《禮儀憲章》第7條)。大部分信友——包括神父及主教——都不知道大公會議的這項教導。一如他們不知道真正朝拜天主的人不是那些按自己的意見和創意去改革禮儀,使之吸引世俗的人,而是那些以福音的深度去改革世界,使它能夠接解禮儀, 這禮儀其實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由永遠到永遠地舉行的禮儀的一個反映。[因此,世間的禮儀應相似天堂上的禮儀。我們感到不熟悉,不正正是因為我們要更加努力擺脫世俗,學習天上的事物嗎?] 一如本篤十六世經常強調, 禮儀的根是朝拜,因此這根也是天主。 所以我們非常有需要意識到這由大公會議時間已嚴重而廣泛着影響禮儀及教會自己的危機,因為天主及對祂的朝拜已不在是禮儀的中心,人和他們在感恩祭中可以「做」些事情使自己忙碌的能力卻成了禮儀的中心。即使今天, 很多的教會領袖低估了教會正在經歷的嚴重危機:信理、道德及紀律教導的相對主義、神聖禮儀中的嚴重違規,去神聖化及蔑視、以及單純以社會學及橫向的目光去看教會的傳教任務。 [樞機不單單說現今教會在禮儀方面的危機,而是指出很多教友的信理出現問題、道德出問題,目光缺少了超性的幅度,只剩下社會學的橫向幅度。] 很多人相信並一直以來大聲宣稱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為教會帶來了一個真正的春天。然而,越來越多的會領袖視這「春天」為一個對歷代流傳的習俗 (centuries-old heritage) 的抗拒及放棄,甚至是從根本上質疑她的過去及傳統 (past and Tradition)。政治化的歐洲因她摒棄或否認其基督信仰根源而被指責。[聖若望保祿二世在2003年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瞻禮前所頒布的宗座勸諭《歐洲的教會》( Eccleisa in Europa)稱歐洲文化變得使人的生活忽視天主,彷彿天主並不存在,是「靜默的背教」(“silent apostasy”) ] 但首先摒棄自己的基督信仰根源及過去的,無疑地就是大公會議後的天主教會。 有些主教會議甚至拒絕忠誠地翻譯《羅馬彌撒經書》的拉丁原文。有些則聲稱每一個地區教會可以自行翻譯《羅馬彌撒經書》而不需要按教會的神聖習俗、跟據《真實禮儀》 ( Liturgiam authenticam) 所制訂的方法及原則;卻是按着幻想、意識形態及文化表達,他們說這能夠被人們所理解及接受。但人們渴望被天主的神聖語言所啟蒙。福音及啟示被「重新演譯」(“reinterpreted”) 、「情景化」 (“contextualized”)、及修改配合低落了的西方文化。在1968年,法國梅茲 (Metz) 的主教在他的教區信函中寫有可怖而令人憤怒的話,似乎表達了要跟教會過去完全斷裂的渴望。按該名主教,我們今天一定要重新思考耶穌帶給我們的救恩的概念,因為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及初世紀的基督徒團體其實對福音毫不認識。耶穌所帶來的救贖只有到了我們這個年代才能夠被理解。以下便是這梅茲主教的大膽而令人驚訝的話:
世界的轉化 (文明的轉變) 教導並要求改變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救贖的概念;這轉化啟示給我們:之前教會對天主計劃的理解,即在現今改變之前,於福音化方面是不足的……沒有一個年代能夠像我們一樣有能力理解兄弟般生活的福音化理想。3
有着這樣的目光,在禮儀、教理、及倫理方面的災難、毀滅及戰爭緊接發生而持續到今天實在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宣稱沒有一個年代能像我們般有能力去理解「福音化理想」。[彷彿自己是整個歷史中最有智慧的人。何其自大。] 很多人拒絕去面對教會藉刻意破壞教理、禮儀、倫理、及牧民的基礎所做的自我毀滅。當越來越多的高級教士盲目地稱許一些已被遣責了一百次的教理、倫理、及禮儀的明顯錯誤、及那些會破壞天主子民剩餘無幾的微小信仰的行為,當教會的呼聲劃破這個低落世界的風浪,海浪衝破本身已浸滿了水的船隻,越來越多的教會領袖及信友大叫:「 Tout va très bien, Madame la Marquise!」(「一切都很好,我的女士!」這是1930年代一首流行曲的重唱歌詞,一個貴婦的員工向她報告災難時都會這樣回答。) 但現實卻相反:事實上,拉辛格樞機說:
教宗及會議神長們期待的是一個新的公教團結,然而我們遇到的卻是紛爭——用保祿六世的話說——始乎以由自我批評走向自我毀滅。曾經期盼着有新的熱忱,然而很多時出現的情況是以沉悶及灰心。曾經期盼着往前踏步,然而很多人卻發現自己面對着一個逐步低落的過程,這很大程度都是以「梵二精神」為口號的呼籲下進行的,這實在不斷的抺黑了大公會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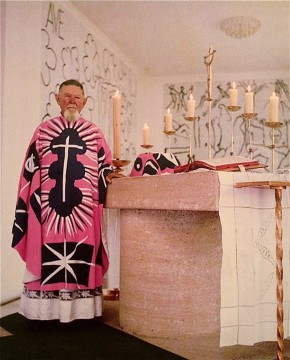
「沒有人能認真否認這些關鍵的事情」以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引起的禮儀戰爭 (liturgy wars)。5 今天我們已發展到,藉着將神聖的《羅馬彌撒經書》拋棄給文化多元及禮儀文字堆砌的實驗。這裏,我很高興地恭喜一項繁重而精彩的作品的面世,就是藉 Vox Clara 、各個英語、西班牙語、韓文……的主教團等等,他們完滿地按着《真實禮儀》的指引及原則忠實地翻譯了《羅馬彌撒經書》,而教廷的禮儀聖事部亦給予了 recognitio[確認]。
在我的著作《 God or Nothing》出版之後, 人們問我關有這個經常在過去幾十年分裂天主教徒的「禮儀戰爭」。我解說這是一個暗喻,因為禮儀應該是天主教徒在體驗真理中、信德中、愛德中合一的最優越的場合,因此在舉行禮儀的同時在心中懷着兄弟間的不和及仇恨是不可想像的。 此外,耶穌不也表達了極高的要求,要我們先去跟兄弟們和好後才去祭台獻上自己的祭品嗎?
反之,禮儀本身促使信友,在飽嘗逾越奧蹟之後,虔誠合作 6;禮儀是在祈求,使信友「在生活中實踐他們以信德所領受的」,在聖體中,重訂天主與人類的盟約,推動信友燃起基督的迫切愛德。所以,從禮儀中,尤其從聖體中,就如從泉源裏,為我們流出恩寵,並以極大的效力,得以使人在基督內聖化、使天主受光榮,這正是教會其他一切工作所追求的目的。 (《禮儀憲章》第十節)
禮儀就是跟天主的面對面的相遇,在這之中我們的心必須純潔不帶任何仇恨,禮儀假設了每一個人在每一方面都是被尊重的。 雖然必須再次強調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從沒有要求要將過去變成白板 ( tabula rasa) 並且廢除聖庇約五世的彌撒經書,這經書孕育了這麼多的聖人,當中包括了必須一提的三位可貴的聖人如亞爾斯的神父聖若望.維雅納 (St. John Vianney, the Curé of Ars)、聖庇護.皮耶牧雷爾奇納 (五傷聖庇約神父, St. Pius of Pietrelcina / Padre Pio) 、巴拉格爾的聖施禮華 (St. Josemaria Escrivá de Balaguer),但這明確地代表着,與此同時必須推廣大公會議所渴望的禮儀更新,因此禮儀書按着《禮儀憲章》更新,尤其是稱為屬真福保祿六世名下的《彌撒經書》。而 我要提出,無論是在舉行普通形式或特殊形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給信友他們有權得到的:就是禮儀的美、它的神聖、靜默、收歛心神、神秘的幅度及朝拜 (the beauty of the liturgy, its sacrality, silence, recollection, the mystical dimension and adoration)。禮儀應該將我們放在與天主面對面的、親密的「個人/位格關係」中 (personal relationship)。它應該將我們置於至聖聖三的內在生命之中。說到 usus antiquior (舊禮)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伴着《歷任教宗》的信件這樣說:
在緊接梵二大公會議 之後的時期,人們推斷,請求採用1962年彌撒經書的,將局限於自幼已採用它的較年老的一輩,但現時證實,青年人亦發現了這種禮儀形式,並被它吸引,且從內裡找到一種特別 適合他們與至聖聖體聖事相遇的方式。
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現實,我們時代的一個真實記號。當年輕人缺席了神聖的禮儀,我們一定要問我們自己:為甚麼?我們一定要確保按 usus recentior (新禮) 所舉行的慶典同樣地能夠協助這一種相遇,引領人在走在 via pulchritudinis (美的道路) 之上,藉她的神聖禮儀而領人到生活的基督及她教會今天的工作當中。 事實上,感恩祭不是甚麼「朋友間的晚餐」,一個團體的聚餐,卻是一個神聖的奧跡、我們信德的偉大奧跡、我等主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贖的慶典、耶穌為將我們由我們的罪惡中解放出來而死在十架上的紀念。 因此,舉行神聖彌撒是很適合用着聖維雅納、五傷聖庇約神父、及聖施禮華的美和熱忱,這是為困難卻有效地到達一個在禮儀中修和的必要條件。7 因此,我堅決地拒絕浪費時間去以一種禮儀去對抗另一種禮儀,或以聖庇約五世彌撒經書對抗真福保祿六世彌撒經書。反而,問題卻是我們要讓我們由所有的,無論拉丁或東方禮,禮儀形式所獲益,從而進入禮儀中偉大的靜默當中。[樞機對信友的建議:不要花時間在攻擊某一禮儀,而應花時間花精力學習禮儀中的靜默。樞機的新書《靜默之力量》中正正表示,現在是噪音的霸權,信友失去了靜默的能力。] 事實上,沒有靜默的神秘幅度以及缺乏一個默觀的精神,禮儀只會繼續是一個仇恨分裂的機會、意識形態的衝突、以及那些聲稱握着某些權威的人對弱小的一種公開的侮辱;卻成不了我們與主團結及共融的地方。因此,禮儀不能是一個衝突和互相仇恨的機會,卻應該將我們眾人都達到對於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並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長進,而歸於那為元首的基督 (參閱 厄弗所書 4:13-15) 。8
眾所周知,著名的德國禮儀專家 甘博蒙席 (Msgr. Klaus Gamber) (1919-1989) 用 「 Heimat」一詞來形容在彌撒聖祭圍繞祭台的天主教徒的共同的家或「小家園」。神聖的氣氛滲透並灌溉着教會的禮儀,這氣氛是和禮儀不可分割而相關的。在近幾十年,很多很多的信友被表面的、嚴重經驗主義的禮儀慶典所虧待及大大的困擾着,甚至他們不再認得他們的 Heimat ,他們共同的家,而他們當中最年輕的甚至從不認識這家園!多少人靜靜地離去了,尤其是他們當中最微小最卑微的!他們某程度上成了「禮儀無國藉者」。 (羅馬禮的)兩種形式都有關的「禮儀運動」目的就是為了給他們恢復他們的 Heimat ,並將他們領回 他們的 共同的家,因為我們都很清楚,遠遠先於《歷任教宗》的頒布,拉辛格樞機早已在他的聖事神學中,指出教會中的這個危機,而這削弱信仰的這個危機很大程度上來自我們如何對待禮儀;按古老的說法: lex orandi, lex credendi ﹝信仰律即祈禱律﹞。這未來的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為甘博蒙席所著的法文版權威性著作, La réforme de la liturgie romaine(英文版為 The Reform of the Roman Liturgy, 即《羅馬禮儀的改革》),寫序時這樣說,如下:
一個年輕的神父最近給我說:「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一個新禮儀運動。」這裏所表達的關注,在今天只有一些刻意膚淺的人才能夠無視。這個神父關注的不是要贏得一些新的大膽的自由:有甚麼自由還沒有被人自大地取用了?他所想的是我們需要一個由禮儀本身出現的新開始,就如禮儀運動在它還符合它真正本質時的意願一樣,當時它不是要編新文本或創造行動或形式,卻是要重新發掘它活着的核心,就是要穿透一切禮儀的一切組織般,使禮儀慶典本身能夠由它的本出發。禮儀改革在它實際的執行中,已遠遠偏離了這源頭。結果不是重生而是破壞。 一方面我們有一個退化成表演的禮儀,嘗試使禮儀變得有趣:我們在試著用時尚的創新及引人注意的道德老生常談、短暫成功的禮儀創作、甚至有一種更誇張的退縮態度:逃避那些在禮儀中並非尋找靈修「主持人」,找尋跟生活天主相遇的人,在祂面前所有的「創造」都沒有意,因為這相遇本身就能讓我們到達那存有的真正富饒。 另一方面,禮儀的壯觀總令人觸動,但當對禮儀形式的保存走到了極端,就變成了一個困執的孤立而最終除了憂愁之外甚麼也不留下。 當然這兩極之間,仍有很多神父和他們的教友以尊敬及隆重舉行這新的禮儀;但他們卻被這兩個極端的人所質疑,而教會缺乏內在的合一在很多錯誤的例子中,使他們的忠信看似單純是新保守主義的個人品牌 (a personal brand of neo-conservatism)。因為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禮儀要再一次為我們成為教會的社群活動、要脫免任意態度的話,新的精神意念是必要的。 一個人不能「創造」 (“fabricate”) 一個禮儀運動,一如一個人不能「創造」一個生物,但人可以為它的發展作貢獻,就是重新汲取禮儀的精神,並公開地保衞他所領受的。
我想這一段長引述,既準確亦清晰,應該對你們很有意思;在這研討會的開端,也能幫助你們開始反思《歷任教宗》自動手諭喻這「未來的泉源」( “die Quelle der Zukunft”) 。事實上,容許我向你們表達我長久以來的一個信念: 羅馬禮儀,在兩種形式的相互配合下本身就是著名德國禮儀學者 若瑟.雲格曼(Joseph Jungmann, 1889-1975) 所說的「發展的果實」,可以開展眾多神父及信友長時間等待着的「禮儀運動」的決定性一步。 從那裏開始?請容我向你們建議以下的三條路,我總結它們為三個字母:英文及法文是 SAF —— silence- adoration-formation,而德文就是 SAA ——Stille-Anbetung-Ausbildung 。 首先, 神聖靜默,我們沒有它就不能跟天主相遇。 在我的著作《靜默之力量》([英]The Power of Silence, [法]La Force du silence)中,我寫道:「在靜默中,唯有人類跪下來傾聽並朝拜天主,他才能獲得他的高貴及他的宏偉」(n. 66) 。 接着, 朝拜,在這方面我引述在同一本書中記載我自己的靈修經驗,《靜默之力量》:
我自己來說,我知道我經歷過的所有重要時刻都是我在黑夜中跪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寶血的至聖聖體之前的那些最無可比擬的時間。可以說 我被天主所吞下了,並被祂的存在所全面包圍着。我現在希望僅屬於天主,投身於祂的愛中。但,我也知道我是如何的貧窮,離上主的愛多遠,祂愛了我,且為我捨棄了自己 (參閱迦拉達書 2:20)。(n.54)
最後, 禮儀培育 基於信仰或教理的宣告,這可參考《天主教教理》, 它保護我們免受那些渴望「創新」的神學家的有學識的詭辯 (learned ravings of some theologians who long for “novelties”) 所影響。 與此相關,我也在2016年7月5日為第三屆「神聖禮儀」國際講座,常被戲稱為「 倫敦發言」(“London Discourse”) 中所說過了:
最根本的禮儀培育是讓人沈浸於禮儀,並進入我們慈父至深的奧秘內。這就是在問怎樣才能生活於禮儀的一切富饒中,至使我們酣飲於其泉源後,常渴望其喜樂、其秩序與美麗、其寧靜與默觀、其歡躍與朝拜,並渴望它將我們親密地與主連結的能力。就是這位主,在教會的神聖禮儀儀式裡裡外外工作。9
在這全球的背景前,對基督在十字架上服從之死的信德精神及與其共融, 我懇切請你們很小心地應用《歷任教宗》;不要當它是負面,落後的方法去回望過去,或用作築牆並自成一國,但要視它為一個重要且真實的貢獻,有益於現在及將來教會禮儀生命,也有益於我們這個世代的禮儀運動,由此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在這裏汲取眾多真善美的事物。
我想以本篤十六世在2008年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瞻禮講道辭的結尾中的啟發性說話去結束這個開端辭:「當整個世界成為天主的禮儀,當它真實地成為朝拜,它就達致它的目標而變得安全完整。」
謝謝各位靜心聆聽,並願天主降福你們,以祂靜默的存有充滿你們!
羅伯特.薩拉樞機 聖座禮儀聖事部部長
原文腳本:
-
“Aggiornamento” 在意大利文中解作「更新」。我們慶祝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五十周年,因為它是在1963年12月4日頒布的。
-
Joseph Ratzinger, Milestones: Memoirs: 1927-1977, translated by Erasmo Leiva-Merikakis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8), 148.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change of civilization) teaches and demands a change in the very concept of the salvation brought by Jesus Christ; this transformation reveals to us that the Church’s thinking about God’s plan was, before the present change, insufficiently evangelical…. No era has been as capable as ours of understanding the evangelical ideal of fraternal life.” Cited by Jean Madiran, L’hérésie du XX siècle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NEL], 1968), 166.
4. Joseph Ratzinger and Vittorio Messori, The Ratzinger Report: An exclusive interview on the state of the Church, translated by Salvator Attanasio and Graham Harrison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5), 29-30.
5. Joseph Ratzinger, Principles of Catholic Theology: Building Stones for a Fundamental Theology, translated by Sister Mary Frances McCarthy, S.N.D.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2), 370.
-
參閱復活節守夜慶典及復活主日的領主後經
-
參閱天主教網站 Aleteia 的訪問, 2015年3月4日
-
參閱跟 La Nef 的訪問, 2016年10月,問題9
9. Cardinal Robert Sarah: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Sacra Liturgia Association, London. Speech given on July 5, 2016. See the Sacra Liturgia website: “Towards an Authentic Implementation of Sacrosanctum Concilium”, July 11, 2016. http://www.sacraliturgia.org/2016/07/robert-cardinal-sarah-towards-authentic.html 中文版由《樂山樂水》及《號角報》分別於 網上 及實體報紙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