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山樂水》早前 介紹 過禮儀及聖事部 (Congregation of Divine Worship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Sacraments) 有新的部長 (Prefect) ,他是來自畿來亞的 羅伯特.薩拉樞機 (Robert Cardinal SARAH)。最近他有一篇文章《 Silenziosa azione del cuore》被譯成英文,引起很大迴響。現筆者以有限的語文,由 Adoremus.org 英文譯文拙譯為中文,望能拋磚引玉,讓各位讀者反思。筆者的 重點 及[評論]。
[2016年7月29日更新:修正了某些專有名詞的譯法]

- 原文意大利文《 Silenziosa azione del cuore》刊登於6月12日 L’Osservatore Romano (《羅馬觀察報》),英文翻譯 (The Silent Action of the Heart)來自 Adoremus 2015年7月號,由Christopher Ruff 所翻譯。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會在保祿六世頒布五十年之後終於會被閱讀了嗎? 事實上,《禮儀憲章》不是一份簡單的改革的「餐單」目錄,而是一切禮儀行動的真正及實質的「大憲章」 ( Magna Carta)。[樞機作了一個很大膽的宣告,他在暗示很多人口中提到的「禮儀改革」並不出自大公會議!這樣的話,這些「改革」又出自誰的意思?]
在這《憲章》中,大公會議給了我們一個方法論 (methodology) 的精修班。大公會議並沒有滿足於一個紀律性及外在性的方法去接近禮儀,而是召集我們去默想禮儀的本質。教會的做法往往是源自她由啟示中所領受及默想的。 牧民的做法並不能和信理分道揚鑣。
在教會,「行動導向默禱」(參閱第2條)。這大公會議的《憲章》邀請我們去重新發現禮儀行動的聖三根源。確實,大公會議確認了贖世主基督的傳教使命 (mission) 及教會的禮儀使命 (mission) 的連續性。「猶如基督為父所派遣,同樣祂又派遣了宗徒們」,「並且要他們以全部禮儀生活所集中的祭獻與聖事」以使他們能「實行他們所宣講的救世工程」(參閱第6條)。
因此「行動中的禮儀」就是「行動中的基督」。禮儀的本就是 actio Christi (基督的行動):「主基督救贖人類,完善地光榮天主這件事業」(參閱第5條)。祂是大司祭,真正的主體,真正的禮儀主角 (參閱第7條)。 如果沒有在信德中緊隨這重要的宗旨,就有危機將禮儀矮化,成為一個人的行動、成為一個團體的自我慶典。[請在這裡停下來想想,大家可想想自己堂區有否陷入這危機?]
相反,教會真正的工程包括進入基督的行動,親密地參與祂在父所領受的使命 (mission)。因此,「祂的人性與聖言的位格相給合,成了我們得救的工具」,藉此「給了我們敬天的圓滿境界」 (第5條)。教會,即基督的身體,必須成為聖言手中的工具。
這就是大公會議《憲章》中 participatio actuosa (主動參與) 概念的終極意義。對教會來說,參與包含著要成為基督司祭的工具,藉此參與祂聖三的任務(mission)。教會作為基督的工作主動地參與祂的禮儀工作。以這層意義來說,「獻祭會眾」這等用詞有一定程度的模糊,並需要小心理解。(參閱《救贖聖事》訓令 ( Redemptoris sacramentum) 第42條)。 故此 Participaio actuosa 一定不可以理解為「要做些甚麼」。在這點,大公會議的教導常常被扭曲。 反而重點是,要讓基督掌握我們並在祂的祭獻中聯繫著我們。[樞機毫不掩飾地指出,很多人說為了主動參與,就要讓教友唱歌、做動作……這種說法違反了《禮儀憲章》。]
故此,禮儀的 participatio (參與)必須被理解為來自那「常與其教會同在」的基督的恩寵 (禮儀憲章第7條)。 是那佔有著首位的祂採取主動。教會「稱呼祂為自己的主,並通過祂向永生之父呈奉敬禮」(第7條)。[在我們平日的禮儀中,教友或主祭有沒有搶了主動的位置?]
司祭因此必須成為讓基督照耀的工具。 正如我們聖父教宗方濟各最近提到,主祭不是一場表演的主持,他一定不可以尋求會眾的肯定,如同會眾被召主要是為和他對話般站出來。相反,進入大公會議的精神就是 要隱沒自己,離開聚焦燈。[我們有見過一些彌撒,講道像棟篤笑、感恩經像朗誦、成聖聖體像演戲、平安禮走足全場嗎?他們是否符合樞機所說的「隱沒自己,開聚焦燈」?] 和一直在流傳的說法相反,以下的做法是完全合符大公會議的《憲章》,而事實上是非常合適的,就是:每個人,司祭及群眾,在懺悔禮、誦唱光榮頌、禱文、及感恩經時都一起轉向東方,為能表達對參與朝拜及基督所完成的救贖的渴望。這做法應該在主教座堂中設立,那裡的禮儀生活必須是模範。(參閱第41條)。[樞機表明,朝東舉祭 ( ad orientem) 是完全正確,而且是模範。這不是甚麼「神父用背脊對著教友」,而是主祭和信友同一方向舉祭!]

當然,在彌撒的其他部分中,司祭,以 persona Christi Captis (以基督元首的身份)行動,跟群眾進入配偶性的對話。但這「面對面」只是為了導向跟天主的「面對面」,這透過聖神的恩寵,將變成「心對心」。大公會議因此提議另外的方法去促進參與:「歡呼、回答、詠頌、對經、歌唱,以及身體的動作、姿態」(參閱第30條)。[樞機並不是鼓勵教友呆呆地參與禮儀,而是有相應的回應;但這回應不是為了教友間的友誼,而是信友跟天主的友誼。] 倉促和過於人性地閱讀《憲章》達致一個結論,就是信友必須經常有事可做。 被科技所塑造及媒體所眩暈的當代西方思想希望將禮儀變為利益主導的產物。在這精神中,很多人嘗試將祭典弄得慶祝似的。出自很多牧民上的動機,禮儀人員有時引入很多世俗元素於慶典中。 我們不是見證了越來越多的證道、動作、及鼓掌嗎?這被想象為可以培育信友的參與,而事實上它在將禮儀矮化為人的玩物。[本篤教宗也提過,在禮儀中出現掌聲就代表禮儀的核心由天主變成了人,代表禮儀失去了焦點。]
「靜默不是德行,嘈音不是罪,這是正確的,」多默.牟敦說「 但那現代社會的[或有些非洲的感恩祭禮儀]的騷動、混淆和不斷的嘈音是它最大的罪過的氛圍的表現:它的不信神,它的絕望。這宣傳(propaganda)的、無盡爭辯的、謾罵的、批判的、或只是碎碎唸的世是,是一個不為甚麼而活的世界…… 彌撒成為喧嚷及混亂;祈禱則成為外在或內在的噪音。」 (Thomas Merton, The Sign of Jonas[San Diego: Harcourt, Inc., 1953, 1981], passim)。[我們有因著世俗精神的入侵,使彌撒和祈禱變成混亂及噪音嗎?] 我們在慶典中沒有預留空間給天主,是在冒著真正的危險掉進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的誘惑。他們在自己的方法及限制來試圖創造朝拜的祭儀,我們不要忘記他們最終就是俯伏在金牛偶像前。[這正正是本篤十六世在其《禮儀的真諦》中所警告的:如果我們以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天主的方法,我們就只是拜金牛的以色列人。]
要聆聽大公會議的時候到了。禮儀是「為敬禮至尊的天主」(憲章第33條)。只有在它完全地指向敬禮神聖及光榮天主的時候,它才能培育並教導我們。 禮儀實確將我們放置於神聖的超性當前。真正的參與表示我們在「奇異感」(amazement)中得到更新,這是聖若望保祿二世非常重視的。(參閱《活於感恩祭的教會》第6條)。 這神聖的奇異感,這喜悅的崇敬,要求我們在至尊天主前保持靜默。 我們經常望記這神聖的靜是大公會議指出以培育參與的一種方法。[在彌撒中,我們有珍惜神聖靜默的時間嗎?而在舊禮彌撒中主祭低默念整段感恩經,也是為了以神聖靜默將信友導入這偉大奧跡。]
如果禮儀是基督的工作,主禮有需要加插自己的評論嗎? 我們必須記得,當《彌撒經書》准許註解的同時,這一定不可以變成一個世俗的人性的論述、對時事或多或少的宣講、或向在場的人一個尋常的打招呼,但應是一個簡短的勸喻召人進入奧跡。(參閱《羅馬彌撒經書總論》第50條)。[樞機的意思是,在彌撒中「各位早晨!」這類的對答是不應出現的。]
在於講道,它也同樣是一個禮儀行動,有自己的規則。 在基督的工作中的 participatio actuosa 要求人去放下這世俗的世界而進入「最卓越的神聖行為」(《禮儀憲章》第7條)。事實上,「我們仍在在人世間,帶點傲慢地宣稱進入神聖」(Robert Sarah, God or Nothing, Ignatius Press, Chapter IV)。
在這意義上,如果我們教堂聖所的用途不限於神聖敬禮,人以世俗的衣裳進入這聖所,在建築上神聖空間沒有被清晰地劃分出來,這是非常不合適的。 並且,由於大公會議也這樣教導,基督在其聖言宣讀時也臨時,當讀經員沒有以其衣著顯示他所講讀的是天主聖言而非人的說話是,這是同樣地有害的。[樞機在這裡解釋了「神聖空間」的概念]
禮儀在根本上是屬於奧秘及默思的現實,因此是超越了我們人性的行動; 甚至 participatio 也是天主的恩寵。它要求我們向被舉行的奧跡保持開放。因著這理由,《憲章》推擴對禮節的圓滿理解(參閱第34條)並在同時要求「 信友們能用拉丁文共同誦代或歌唱,彌撒常用經文中屬於他們的部分」(第54條)。[我們不應以為「參與」是人的能力,這其實也是天主的恩寵。而樞機也特別提到信友應該學習禮儀中的常用拉丁文。這是大公會議的訓導,希望本地堂區也能多推廣。]
在現實,對禮節的理解不是單單靠人性理智就能夠達到的,就好像把人性理智說成可以理解一切,明白一齊,掌握一切。 對神聖禮節的理解是 sensus fidei (信德意識)的效果,它透過標記表示著生活的信德,它的理解是關係重於概念。 這樣的理解要求人以謙遜去接近這奧跡。[學習禮儀的先決條件是謙遜,明白靠自力沒法接近這奧跡。唯有這樣,信德之門才能夠開啟。] 但我們會有勇氣跟隨大公會議到這一點嗎? 然而只有這一種閱讀,被信德所光照的,構成福傳的基礎。實在的,「禮儀又能把教會顯示給教外的人,好像樹立於各國之間的旌旗,將散居的天主兒女,齊集麾下」(第2條)。它必須不再成為違反教會規則的地方。[我們有勇氣將現在錯誤的禮儀習慣修正嗎?還是我們寧可隻眼開隻眼閉,讓錯的繼續錯下去?樞機說得對,這需要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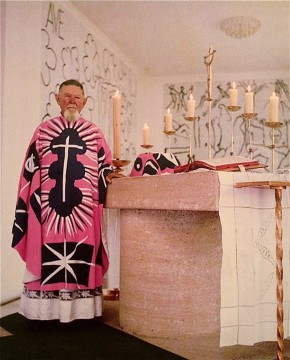
再針對地說,禮儀不可以成為分裂基督徒的機會。以辯證法去閱讀(dialectical readings)《禮儀憲章》,及「斷裂詮釋法」(hermeneutic of rupture) 在不同的意義上都不是信德精神的果實。大公會議沒有意圖由傳統所繼承的禮儀模式中斷裂出來——事實上,她渴望深化它們。《憲章》制訂「新的形式,是由現存的形式中,有系統的發展而來」(第23條)。[有關 hermeneutic of continuity 和 hermeneutic of rupture ,之前也有 談論 過,請看該文及其第一點註解。]
在這意義上, 那些根據 usus antiquior (舊禮)舉行慶典的人不能抱有反對 [大公會議] 的精神,而要根據《禮儀憲章》的精神去舉行慶典。同一道理,「視羅馬禮特殊形式是從不同於新禮的神學所發展出來的」也是一種錯誤。 而我們可希望《彌撒經書》將來的版本能夠包括 usus antiquior 的懺悔禮及奉獻詠,以表明 兩種禮儀模式互相光照,是連貫而不是對抗的。[就是說,開傳統彌撒的人不能視《禮儀憲章》是錯誤的,但同時新舊禮儀是出自同一的神學。我們有沒有以為現在舉行舊禮彌撒是錯誤?我們有沒有以為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違反了信理及傳統?] 如果我們活在這一精神中,禮儀將不再成為抗爭及批判的核心,而我們將終於能夠主動地「參與那在聖城耶路撒冷所舉行的禮儀,我們以旅人的身份向那裡奔發,那裡有基督坐於天主的右邊作為聖所及真會幕的職司」(第8條)。
樞機的這篇文章,可能替很多人打響了警鐘:原來我們平常的禮儀有很多地方都未必完全符合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教導,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但這不是說大家在這個主日馬上回堂區叫神父將一切未如理想的地方立刻改變。反而大家應先退一步,好好思量自己對禮儀的認知。在適當時候再跟堂區神父及禮儀小組討論及安排一系列的改善措施,也可以邀請神父在主日講道中加強禮儀的教理,及講解改變堂區禮儀習慣的原因。
禮儀小組應該對自己及堂區信友有點信心,相信自己能夠在改善禮儀的同時,可以幫助到信友理解禮儀的真正意義。但這應該要逐步來,就如天主將真理逐步啟示及人;我們也應有耐性,切勿一步登天。將禮儀在短時間內改變的惡果,上世紀已試過一次,我們不必現在再試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