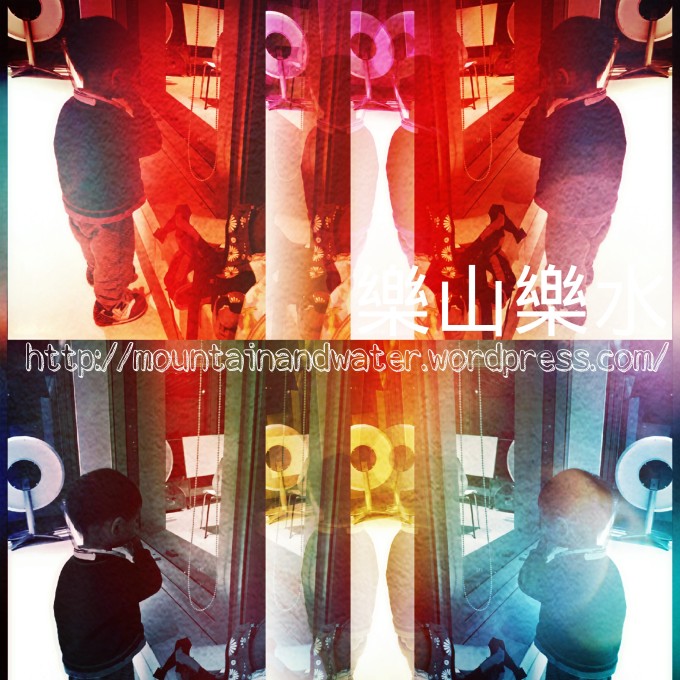
早陣子的一篇 文章 講及小兒到沙灘的經驗和反思,自覺學習了不少新的東西和可行性,也輾轉勾起了自己藏在心裡多年的傷痛,是時候寫出來,好好梳理後,坦然面對,自己也從新出發,希望當個懂得尊重孩子位格,細心的醒目媽媽。(後按:多年後以文字記錄,心還是戚戚然,是筆者太「玻璃心」嗎?)剛好這陣子愈來愈多朋友關心學生情緒抗逆問題(實情是:成人也常壓力爆煲),其實有沒有想過部份壓力是源於家長嗎?來分享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故事。
已忘記了是哪個日子或時間,大概是筆者小學4年級的一個暑假呆呆的等著爸媽下班回家。小朋友一個的呆在家裡,就是無聊極了,那就想想有什麼可動動手的玩意吧。忽發奇想,希望為家人們動動手,做點手工吧,就是小孩最直接為家人表達心意的方式吧。想著想著,家裡好像剛缺拖鞋,就用紙張,慢慢小心地按著爸爸媽媽弟弟鞋履的尺寸,剪剪貼貼畫畫,花了大半天,造了各人一對紙造的拖鞋。自覺滿意極了,就美美的一對對排列在大門,好讓父母回來時能看到這驚喜,逗他們笑笑。(其實還有同系的紙摺出來的衫和家居小物。)
期待了一整天,父母終於回家了,作為繁忙的成人,當然完全無視那幾雙拖鞋吧。小孩當然也忍不住開口,對話如下:
筆:(滿心歡喜的)我今日整咗啲小禮物俾你地吖。 母:嗯,是嗎? 筆:你入門口時看到嗎? 母:沒有留意。 筆:(飛快地從門口把小物端到媽媽前)就是這些拖鞋吖,一對給你,爸爸。。。 母:吓?! 只有死人才會著紙造的東西,活人是不會用紙造的東西。這些只能燒給死去的人。 筆:(呆掉了十秒,當然也心碎,但沒有淚水,大概已習慣了,當務之急是盡快可以扭轉這個做錯事而被不斷罵的危機!) 唔好意思,我不知道活人不能用紙造的東西。 母:哎呀! 正常人又怎會著到這些東西吖,咁唔吉利。。。(下刪一堆批評) 筆:。。。。。。對唔住,唔好意思。 母:係吖。你要記住,只有死人才會用紙造的東西。。。 筆:是的,是的。那些其實是給我的毛公仔造的。我希望他們有新拖鞋著。我只是給你們看看。 母:喔!原來係咁,做俾佢地就無乜所謂既。 筆:係吖。係做俾佢地架。(雖然傷心,但總算有驚無險,總算逃過不斷被罵的情境。) 母:是的,你的功課習作,今天做了多少?。。。
如果要抽離地分析以上的事情,不單單是母親浪費了孩子的好意,同時亦完全踐踏了孩子希望為家人負出的意慾。下意識也是扼殺了其子女培養愛德的機會。漸漸地,不難理解孩子變得自我中心,盡量和家人疏離,減少下次再觸礁的機會。 小孩也得出以下的信息:原來敞開心扉「去愛人」,換來的是如此傷痛,那把就應把心好好的關上,只要不再「去愛人」那就不會「被人」傷害。小孩因此也把心緊緊地關上,不再相信好心好報,或者應為別人多做點事情。 既然母親口裡只顧學業,那就是以行動告訴孩子,只有學業成續,才能值得母親的關注,其他的也彷彿亳無價值。希望討好父母,本來就是孩子的天性。我們成人也喜歡別人欣賞和喜愛吧。當然女兒亦學乖了,不會再做「多餘的事」。要做手工,要分享,要談天嗎?也只會找她最好的朋友,一堆最忠心的毛公仔們。對孩子的傷害,不一定是由體罰所成的。言語是一把往往是雙刃劍,可以狠狠的傷害人的心靈。而要治癒的時間,往往是以年月計算。
漸漸地,家庭也不是避難所或傾訴心事的地方,只能說蠻像社會一樣,光是著眼孩子「成續」或論功過的地方。成人口中的讀書的目標,是永遠難以達到。連續默書10次100分嗎?可惜第11次錯了「標點符號」扣3分,只得97分,那失敗就似烙印般反反複複地被提起:就是因為「那一次」不小心,沒有如常應有的100分。這「失敗」就不斷地掛在父母的咀邊,縱使那原意大概是希望孩子改過, 但當滿分已是份內事情,孩子的世界也不再會有讚賞,只有「不達標」和失敗。 考到10名以內嗎?那目標就馬上變成3名以內。或由「全班」變成「全級」了。
父母是教育子女的最先負責人。 為表現出這個責任,他們首先為子女創立一個家,溫柔、寬恕、尊敬、忠實和無私的服務便是家規。家是培育德行的適當場所······ 給自己的子女樹立良好的榜 樣,是父母一個重大的職責。 《天主教教理 第2223條》
到今天自己成為母親,以上的場境仍是歷歷在目。我們總是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轍,但往往又不經意地,重複著那些不幸和傷害。作父母的,雖不是聖人,但良好的榜樣是重要的。因此也要好好學習梳理自己舊日的情緒和解開往日的心結。父母的身心健康,才能更有力在這亂世去協助孩子。
給那些曾被誤解而受傷害的人們=):
不必期盼人人都「了解」你。那個誤解是天意,為使你的犧牲隱而不顯。聖施禮華《道路》647。

